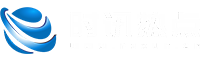教材非“藝術探索”園地,“美”的標準必須建構在社會、文化普遍接受的基礎上
設計兒童出版物需更加嚴謹和審慎
近日,因“五官不協調、表情扭曲”等問題,人教版教材插圖引發社會熱議。對此,人教社迅即發聲,將對相關教材插圖進行更換,教育部也立即部署對全國中小學教材進行全面排查,并將組織專家團隊進行嚴格審核。
而在社交平臺上,“插圖事件”的影響仍在發酵,不少網友反映,“兒童形象丑化”的教材之外,兒童繪本、讀本等出版物也存在諸多問題,一些常識性錯誤和低俗內容并不罕見。
教材為何會“翻車”? 以此為鑒,我們應怎樣盡力杜絕兒童出版物的質量問題?
兒童出版物插圖良莠不齊
“萬一影響孩子的身心發育怎么辦?”“出版社的審核把關呢?”……討論內容從繪畫風格到圖案內容,從設計理念到編校出版流程,相關話題數次登上熱搜。
公眾的關注,“包括批評、建議,應該大都是出于公心的,是促進教育事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總干事張洪波說,社會各方面廣泛討論和發表意見是促進教材質量提升的一個重要環節。
但有關教材插圖的討論也需要條分縷析,需要理性的聲音。記者調查中多位專家表示,應就事論事,把教輔書籍出現的問題都歸于教材也有失偏頗。
今年3月,國家新聞出版署通報圖書“質量管理2021”專項檢查結果,在少兒圖書、教輔材料區塊,100家被抽查出版單位的300種圖書中,編校質量不合格的圖書高達62種。其他各類兒童出版物的質量也同樣受到關注。
無論是審美,還是價值觀的養成,兒童讀物“都會給孩子帶來潛移默化的影響”。有多年繪畫經驗的畫師申陽說,兒童出版物的設計者有責任設計出符合兒童年齡和身心特點的作品,這是保證兒童出版物質量的第一關。
“不過什么是好的插圖,在畫師眼里實際是個市場問題。據我了解,繪制出版物大多由甲方定價,畫師在出版物面世之前結算稿費,議價能力弱,主動性不高,即使銷量很高也未必見得約定了提成。而且出版社的稿件往往量大,時間緊,畫師也會衡量付出和收益是否成正比。”申陽介紹道。
更讓申陽感到無奈的是,市面上的兒童出版物良莠不齊:“質量平平的和質量優秀的銷量差不多,甚至質量有瑕疵的也能出版。”申陽認為,如果作品質量和畫師收益的關聯不夠緊密,那么必然會打擊畫師的積極性。
編審兒童出版物需多些敬畏
審美多元沒錯,但關涉到孩子美育培養的教材更需倍加嚴謹和審慎。插圖質量存疑的教材得以發行并沿用近10年,問題到底出在哪里?這是進一步的追問。
因個人經歷、理念不同,審美體驗有別是正常現象,但教材不是‘藝術探索’,它的受眾是孩子和家長,“美”的標準必須建構在社會、文化普遍接受的基礎上,出版社“對教材編審需多一分敬畏。”在某出版社工作了20多年的資深編輯張亮說。
出版物插圖在編審過程中要經歷“三審三校”,即責任編輯初審、部門領導復審、分管的社領導終審。“教材審校理應更加嚴格。”張亮說。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表示,教師、家長、學生乃至社會各界都有對教材監督和提出建議的權利,一些問題長期沒有解決也說明反饋渠道還需要更加通暢。
“從行業看,兒童出版物插圖質量良莠不齊也與出版行業的市場現狀有關。”張亮透露,由于出版業各環節利潤被不斷壓縮,圖書插圖往往都是責編自己找設計師設計,一幅圖最低可能只有幾十元。低廉的價格導致招標競標流程被省略,出版社出于對成本的考量,除非插圖質量很糟糕,否則基本都能通過。
根據《2021年圖書零售市場報告》,在2021年各類圖書的碼洋構成中,少兒類仍然是碼洋比重最大的類別。“巨大的市場潛力引得出版社紛紛涉水兒童出版物,引進了一些質量良莠不齊的國外兒童書籍。”張亮表示。申陽補充說,這也催生了一大批“賺快錢”的畫師,以模仿畫作入市,導致兒童出版物市場魚龍混雜。
激發插圖創作的源頭活水
作品被選入教材對畫師是一種肯定,但教材也存在索圖的現象。“一些入選插圖并不署作者名字。”申陽認為,只有重視版權,畫師才會有創作積極性。
教材中選用的插圖分為自行設計、委托設計和法定許可三種。出于國家教材建設的需要,九年制義務教育和國家教育規劃的教材編寫出版單位可以根據教學大綱,對已發表的文字、美術攝影、音樂作品等,實行“先使用后付酬”,標準是2013年國家版權局和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布的《教科書法定許可使用作品支付報酬辦法》,每幅作品200~400元。
據教育部數據,2021年我國九年制義務教育在校生達1.58億,高中階段在校生達4162萬。語文,歷史、政治三科教材由教育部統編之后,每年單科統編教材的發行量達上千萬冊,依舊按照2013年的付酬標準給付報酬。張洪波坦言,有關部門應該考慮根據發行量激增這一客觀事實提高教材選用已發表作品的稿酬標準。
指望某一個機構來統編審核所有教材,難度是很大的。儲朝暉相信,豐富多樣的充分競爭,開放的選擇機制,才能優勝劣汰。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關鍵詞: 藝術探索
責任編輯:Rex_01